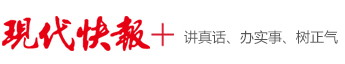如何准确概括或定义李宏伟的小说?这似乎是一件格外困难的事情。
同为作家的李洱思索良久,最终只能用否定句的形式来肯定这种呈现出异样形态的小说:“李宏伟写的不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小说,无论是纯文学还是通俗小说;也不是我们所理解的科幻小说……李宏伟的‘虚构’是真正的‘虚构’,当这种‘虚构’以文本实体的面目出现,它就不是一面简单的镜子,而是一个尚未除尽杂质的晶体在向各个方向闪光。对于不同的读者而言,如何理解这样的小说,有赖于你看到的光是从哪个方向射过来的。”

△《信天翁要发芽》 李宏伟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在读者对李宏伟小说的评价中,常常出现的关键词是“思想实验”“平行时空”。十年都不会驻足陆地的信天翁,何以使它扎根,又何以使它发芽?归根结底,人要在哪里发芽?在新作《信天翁要发芽》里,“思想实验”的场域再次展开。
四场表演呈现出一个城市的编年史和众生相:统治者的欲念与欲盖弥彰,追随者的进退与周旋,反抗者的沉默与告密者的祈祷,民众则自有一套以不变应万变的生存哲学,面目模糊地播种、收割和歌唱,无论餐桌上是面条、米饭还是面包。传说将军在城市的各个场所,甚至每位市民身上都安装了镜子,让他可以看到城市的每个角落;一年一度的千层衣仪式,十二岁童子要穿起一件又一件城市建设者们的衣服,以穿上衣服的多少来预示城市的未来;一座原始丛林与城市构建起互相指涉的镜像,狮王的王冠丢了,命令手下狼、狐狸、鬣狗和鹰带领群兽迁徙……
“《信天翁要发芽》如一棵倒置生长的巨型花树,沿着想象开出的硕大花朵、叙事编织的巍峨树冠、逻辑浇灌的挺拔枝干,我们最终会触摸到根须抵达的每一处切身现实,从摇曳的树影里捕捉属于自己的光阴与命运、劳作与时日。”这样似乎仍然无法概括李宏伟的小说,就像书中写到的“游动旋转门”,也许要窥破它的出现并进入门内转上一圈,才能获得其中强大的能量。

李宏伟
生于四川江油,现居北京。已出版长篇小说《信天翁要发芽》《国王与抒情诗》《引路人》《灰衣简史》《平行蚀》,小说集《暗经验》《雨果的迷宫》《假时间聚会》,诗集《有关可能生活的十种想象》《你是我所有的女性称谓》。获第二届吴承恩长篇小说奖、《亚洲周刊》2017年度十大中文小说、第十届春风悦读榜“春风科幻奖”、第七届郁达夫小说奖等诸多奖项。作品入选收获文学榜、城市文学榜等榜单。
呈现历史纷乱中的恒定
读品:请谈谈《信天翁要发芽》的创作契机。您曾经提到书名关联着两句诗,一是波德莱尔的《信天翁》,一是艾略特的《荒原》。前者关乎整首诗营造出的意象:落在甲板上的空中王者,只能成为被戏弄的对象;后者主要关乎“去年你种在你花园里的尸首/它发芽了吗?”这一句,能具体阐释一下吗?
李宏伟:一部长篇小说的根由其实挺多的,它就像一棵大树一样,不靠独立的根系来支撑,而是有很多看不见的根系在地下埋藏、蔓延。我觉得主要的一个是“信天翁”这个意象,波德莱尔诗中的信天翁始终在我心中徘徊,我也试图为它找到一个甲板。另外一个是“将军”的意象,对像我这样上世纪70年代末出生的中国男性来说,“将军”和这个称呼背后意味的荣耀,包括男性的自我要求或者自我约束都是让人印象深刻的,每一个像我这么大的同龄人小时候应该都玩过士兵打仗的游戏。另外也有对拉美文学以及它所代表的那块土地的想象和理解,拉美历史上的很多革命领袖,很少有像中国古代那样称王、称帝的,通常他们更热衷一个少校、少将之类的称呼。还有一个因素,是我之前写过一个长篇,叫《国王与抒情诗》,这本书中的“将军”某种程度上能够和其中的“国王”这个形象形成一个对位,我对“将军”和“国王”,其实怀着同样复杂的情感,我主要是在尝试理解他们,而不是去憎恨他们。我们生而为人,最重要的还是要尝试去理解这个世界的丰富性和复杂度。
向死而生,或者说死亡当中蕴含的生机是这部小说一个很重要的意蕴,是我希望传递给读者的。这听起来是一句鸡汤话,我想说的是这里其实蕴含着转变,转变其实也是代价——当信天翁开始发芽的时候,就意味着作为动物的信天翁不存在了,作为植物它发芽了,但是这株植物是否还跟信天翁有关?以上基本上都是一些诗意的触发,当然诗意未必是那么温情的了。
读品:书中通过无数种视角去间接讲述将军的故事、描绘他的形象,众声喧哗之后,个人认为书中一个隐在的主角其实是“权力”,无论是“守护者”还是狮王,匪帮大统领或将军,其实都是“权力”不同的呈现形式,在“权力”这一力场的覆盖下,所有人事物都会变形。很想听听您对这个话题的更多思考。
李宏伟:与其说是“权力”,不如理解成代表死亡阴影的暴力更直接一些。书中也提到了将军的那支手枪,大家之所以变形,是因为阴影的逼视太重了,谁都不知道将军和将军的卫队什么时候会发作。其实权力或者暴力不需要无处不在,它只要让你觉得它无处不在就可以了。
读品:但是在垫场的“劳作表演”中,我们又看到力场边缘的人如何自然地婚丧嫁娶、生老病死,权力虽然影响了石榴街区居民的命运,但进入具体的生活、劳作场景中,它又显得如此虚妄。
李宏伟:垫场的“劳作表演”是写作时最鼓舞我,也最让我觉得生机勃勃的一部分。不管外在的东西怎么样,其实大家依旧在生活。抒情一点来说,不管我们整个人类社会经历了多么糟糕或者多灾多难的历史,大家整体上是在往前走的。在历史纷乱中其实也有恒定的东西,我觉得把这一点呈现出来也是小说家的义务。当时我读《黄金时代》的时候非常惊讶和感动,在此之前,我不知道“文革”时期还会有爱情,还可以有那样坦白的、坦率的人与人的交往,作家的重要意义可能就是告诉大家有这样的东西在吧。
唯有表演可以显影真实
读品:《信天翁要发芽》由四场独幕剧构成,每一场的视角和风格都截然不同,您在创作时,是如何构思四场表演的命名和内容排布的?
李宏伟:我们可以把这四场独幕剧理解成整个小说四个不同的声部,或者说一场表演的四个角色。它们有各自要承担的部分,有各自的性格,它们要共同完成一场从“信天翁之死”到“植物发芽”的过渡。从另一个层面来说,这四个部分是在一个城市里,或者说在一个完整的治理结构里可能存在的,或者说我关心的不同部分。“情势表演”更多是普通市民的层面;“立身表演”关涉的人物主要是所谓的精英层面;“辩解表演”关注的是已经被历史覆盖、但又有历史纵深的那一部分;至于“劳作表演”,我们可以说它与另外三场构成了一个互相对立又互相补充的关系,它既是铺垫,也是前导,还是背景。前面三场表演是在相对短暂的时间里存在的,而“劳作表演”则将目光投向了更恒久的存在。
读品:全书的关键词是“表演”,第一部分“(16.将军的话:唯有表演。唯有恐惧)”这一节尤其意味深长,这是将军操控人心的方式,也是您的创作理念。能请您再具体谈谈对“表演”的理解吗?
李宏伟:第一部分“情势表演”相对来说确实比较复杂,我觉得不妨有这么几个理解角度:第一节将军说“你,率先表演”,“你”可以是某一个具体的市民,可以是城市中的无数个市民,“你”当中也不排除有将军。如果这么考虑的话,其实“情势表演”本身就已经是一场群体表演。第16节可以把它当成将军的心声,这场群体表演一定有要传递的信息和各自想要达到的目的,这就会有一些基本的要求,首先表演者们要把表演推进下去,互相不能撕破脸,还要传达各自最想要的东西,这里面还是有一种拉扯在的。此外,从小说的功能或者职能上来说,“情势表演”还给出了一整个城市的全景,交代了前因后果,这座城市的过去、现在甚至未来。因为这部小说是全虚构的,所以它有必要做这些交代。
与其说“表演”在这里是操控人心,不如说它最重要的作用是进行验证。金克木先生谈到赵高的指鹿为马,他认为从政治角度来看,在赵高当时所处的场景下,指鹿为马其实是一个很高明的手腕,通过这种荒谬的、完全名实不副的形式,赵高就能瞬间测试出谁是他的跟随者、谁是他的反对者、谁是犹豫者。书中的表演其实也是这样一个测试。
不是非要如此,是只能如此
读品:书中描述了很多奇特的仪式、神秘的现象,诸如千层衣仪式、游动旋转门、吞食兽竞赛、物行日……读起来引人入胜,很好奇这些构想都是从哪里而来的?您似乎比较喜欢将各种符号融入文本中,作为读者,这样的作品读起来有种解谜游戏的乐趣;身为作者,您使用各种符号的初衷是什么?
李宏伟:我们当然可以感性一点,说是文本的召唤。但要更实在地说,我在这本书里其实想尝试一下把我所有想说的化作形象或者说符号。符号当然会有象征性的含义,但在这个小说里面,我想尝试让所有这些符号关联起来,它们自身就足以构成一场游戏。比如一个小朋友来读,他不会去猜想“千层衣仪式”或者“吞食兽竞赛”背后有没有别的意思,他觉得把衣服不断往身上穿,互相比赛能吃多少碗面之类的读起来好玩就行了。假设有神存在,那我们人类的所有活动对他来说也都不过是一个个符号或者符号的投射,但是这不妨碍我们自得其乐。
读品:《信天翁要发芽》像带有讽刺意味的寓言,了解您的其他作品后,发现《引路人》《灰衣简史》等作品又有不同的形态呈现。探索多样化的写作形式是您创作的目标之一吗?
李宏伟:探索多元化的写作形式是我的一个关注点,但是这种关注的热情,其实是在比较早期的时候,在我写出的第一个中篇集《假时间聚会》里比较突出。但是后来我逐渐更在意自己注视什么,以及如何把我注视的东西准确地传递出来。采用不同形式的写作手法,是为了找到一种更准确的传达方式。所以说不是非要如此,是只能如此。
读品:哪些作家作品对您产生了比较深的影响?
李宏伟:对我影响比较大的作家有两个,一个是加缪,一个是乔伊斯。加缪更多像是一种精神气质的注入,他为我注入了一种存在主义哲学的底色,这种底色并不是绝望的。包括这两年发生的战争,我都会想如果加缪还在会怎么办?他应该会呼吁大家停下来,希望一个人都不要死,即使明知道是徒劳的,我觉得这是作家跟政治家的不同。乔伊斯的艺术雄心,以及雄心背后对自己的苛刻让我印象深刻。他对我的写作生涯有实在的影响,我大概30岁左右的时候胆子大,试着翻译过乔伊斯的书信集,最早有一些朋友知道我在从事文字工作,开始关注,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现代快报+记者 姜斯佳